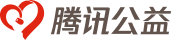体育公园的长椅上,他蜷缩的身影像一片被风雨打落的叶子。黄梦走近时,他抬起枯槁的脸,嘴唇干裂得如同旱地。递过去的食物和水,被他颤抖的双手捧住,几乎是吞咽着完成了几日来的第一餐。他说从异乡跋涉而来,只为找份工,养活山坳里病弱的双亲与寄养在老人膝下的孩子。

我们迅速为他联系了一份工作机会。然而当他站起身,迈开步子时,那条不便的腿拖住了希望——每一步都踏出无声的艰难,也踏碎了这份可能。公司无奈婉拒了他佝偻的背影。

电话拨回那个贫瘠的村庄,听筒里传来叹息:父母常年卧病,土屋四壁空空,唯有一个消息像裂缝里的微光——“若能回来,低保还能接上一条活路。”这“低保”二字,成了寒夜尽头唯一的火种。我们当即协调村委,为他买好次日归乡的车票。
大巴启动时晨雾未散。他攥紧那张薄薄的车票靠窗坐下,窗外流动的街景渐渐模糊。一张车票虽轻,却载得动一个男人沉甸甸的尊严;一条归路虽远,终被无数陌生人的暖意悄然铺平——当车轮碾过晨光,困于绝境的生命,终在故土的守望里寻到了微亮的岸。